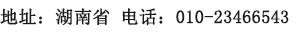作者:吴光范省人大常委会
(原标题:盛产稻谷的“天造水城”——鸭池城名初探(下))
昆明呈贡一景耿嘉摄
种稻与牧羊之辨
前文探索分析鸭池之“池”的彝语地名含义,得出“池”的含义为稻谷。但是,彝语中称“池”(赤)的近音地名,还有另一含义为羊。如师宗县龙庆乡龙庆村委会上、下池布格村,“彝语,‘赤白沽’,‘赤’为羊;‘白’为山;‘沽’为山腰,意即牧羊的山腰,后演化为‘池布格’”(《师宗县地名志》)。昆明市呈贡区七甸村,“七甸”来自彝语“雌甸”的谐音,雌为羊,甸为坝,意为羊多的山间坝子(《呈贡县地名志》第19页)。《罗平县地名志》载:“区革,彝语。区为羊;革为地方。意为牧羊之地。”《富源县地名志》载:黄泥河镇迤更者村委会齐备村,“‘齐备’,意为羊群多得像流水”;营上镇迤启村委会上、下支龙村,“彝语‘支龙’(支为羊,龙为河水),意为河上边彝家养羊的地方”。
如按此解释,则鸭池(押赤)、一期、以扯,含义为建于滇池水边的四周山上多羊的城池。此释有影射昆明部落为牧羊的游牧民族之妙,即《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西自同师(今保山市龙陵县一带),北至楪榆(今大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数千里。”在其迁徙所到之处,便在今之大理、四川盐源、今之云南省会以及贵州普里、安顺一带(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留下了多个“昆明”的地名。但因云南山区辽阔,牧羊之地甚多,并非是滇池边上昆明城的独特景观,上述考释,应以“池”为稻谷之说的证据更为充分,即鸭池城的彝语本义是建于滇池水边的四周盛产稻谷的城池或四周盛产稻谷之水城。
昆明大德寺双塔与绿水河旧影
鸭池城地名的演变
彝语称昆明为鸭池(押赤)变为官方记载之城名,经历了习称地名“鸭池”的形成和向官方记载地名转化的过程。
习称地名“鸭池”的形成。形成时间当早于元兵攻城之时,至少宋代已口传于民间。《新唐书·南蛮传》载:“代宗广德初,凤伽异筑拓东城。”《新纂云南通志》说:“蛮书拓东城,广德二年凤迦异所置也。其地汉旧昆川,故谓昆池。”《南诏德化碑》载:“诏(阁逻凤)候隙省方,观俗恤隐。次昆川,审形势,言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十四年春,命长男凤迦异于昆川置拓东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云南省》载:“广德二年(公元年)南诏置拓东城,取‘开拓东境’之意,为拓东节度驻地。”这是今昆明城有可靠记载的建城之始。之前战国时庄蹻故城,从晋宁石寨山发掘出土的滇王之印和大批墓葬物的考古资料推断,应在今晋城一带。汉代建的谷昌县城,《新纂云南通志卷四十·地理考二十·城池一·苴兰城》:“一名谷昌,在昆明县北十余里,楚庄蹻筑”。《雍正志》:“谷昌废县,一名苴兰城,在昆明县北七里,庄蹻王滇时筑,汉置县,后废,址尚存”。按上述记载,谷昌城在今昆明城西北七至十华里处,有人推测即今黑林铺一带,不在元代鸭池城址。西晋宁州、东晋晋宁郡均治滇池县,在今晋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云南省》第10页),也不在元代鸭池城址。
唐宋之际,昆明已有三面环水之风貌。《滇云历年传载》:“段素兴(大理国第十代王)广营宫室于东京(今昆明),筑春登、云津二堤”,“春登、云津二堤,分种黄白花其上,有‘绕道金棱’、‘萦城银棱’之称”。足见当时的昆明(拓东城),经唐代南诏辟为“东都”和大规模建设后,至宋代大理时期,水利和城市建设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史籍记载可知,鸭池的习称地名是在唐南诏建拓东城、劝丰祐时(公元一年)置鄯阐府和宋大理时扩建鄯阐府后,形成城池三面临水,即东面以盘龙江临水,西面、南面以毗邻滇池临水,城西和城南的沼泽地有蒲草田、螺蛳湾、李家堆、摆渡村(今弥勒寺),城区四周多为稻田,城内外河流清澈、碧波荡漾,莲花盛开,渔舟来往,采莲运鱼,有水乡泽国、高原姑苏之盛,出现采莲河、明波、船房等水乡泽国的地名,在这样的背景下,昆明世居彝族也以自己的语言称其为鸭池等近音地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云南省》昆明市“从大理到元又名押赤城(或作鸭赤城)”是有依据的,可信的。
习称地名“鸭池”向官方记载地名转化。这与阿良、赛典赤的关系较大。前者,方国瑜先生考证甚详。因阿良其父阿琮,“旁通百蛮各家诸书,以为神通之说,且制本方文字”,阿良“继父职”,“忽必烈亲征大理,良迎兵于剌巴江口,锡赉甚厚”(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五卷第页),作为丽江土官和其父“旁通百蛮各家诸书”的教诲,阿良对全省情况当很熟悉,对彝语称昆明为鸭池的习称地名亦应熟悉,在领蒙古军攻占鄯阐城时采用彝语习称地名押赤向兀良合台等蒙古将领介绍的可能性更大。赛典赤在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之前就已广泛调查云南山川形胜、民风民俗、地名城名,此即《新纂云南通志卷五·大事记五》所载:“赛典赤受命,既访求知云南地理者,函其山川城廓、驿舍军屯、夷险远近,为图以进,帝大悦,即拜平章政事。”另外,《元史·卷八·本纪第八·世祖五》载:至元十年(年)“闰六月丙子,以平章政事赛典赤行省云南,统合剌章、鸭赤、赤科、金齿、茶罕章诸蛮,赐银二万五千两、钞五百锭。”可见,赛典赤在出任云南平章政事时已有鸭赤之名,就任后他又亲自将来自土语“不雅顺的地名悉皆改易”,即《元史·卷九·本纪第九·世祖六》载:(至元)十三年(年),“云南行省赛典赤,以改定云南诸多路名号来上。”由此可知,是阿良指称昆明城为“鸭池城”,又经赛典赤上报朝廷并被采纳,于元代延祐三年(年)刊刻入邛竹寺圣旨碑,后为明代宋濂等撰《元史·本纪》《元史·列传·兀良合台传》时编入文献,阿良、赛典赤在此事上所起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昆明船房河张彤摄
往昔之水乡风光
宋元时期的昆明城名“鸭池城”,地处滇池之滨,三面际水,城周坝区和山间水田,广种水稻。其稻乡水城风光,类似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年11月笔者曾亲历威尼斯,乘坐被称为“水上巴士”的小艇由亚得里亚海经河道游于城中。历史上的昆明城也有四海、六河之说。四海即翠湖,旧时由东、西二堤分隔为四,遂称四海,古为滇池海湾,明洪武十五年(年)筑砖城时,将湖圈入城内,称“九龙池”,以“九泉所出,汇而成湖”取名。据《云南府志》载,清初,吴三桂以翠湖为禁苑,“填海子之半建新府,极其壮丽”,名平西王府(洪化府),使今科技宫、省图书馆一带水域全部变为陆地。但当时翠湖仍有水道与滇池相通,可经洗马河(今翠湖西路)、通城河(今省图书馆前至东风西路),过洪化桥(今海逸大酒店附近),至小西门外,从玉带河进入盘龙江,再进入滇池。六河,即盘龙江、金汁河、银汁河、海源河、宝象河、马料河,纵横广布于昆明城乡,构成名副其实的“天造水城”。
历史上,从滇池乘船经多条河流可以直入城内,从各州、府运来的粮食、蔬菜等物产经水路运入城中销售。滇池盛产白鱼,亦经河流运入城内供应市民。因此元人王升在《滇池赋》中赞道:“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蜂屯于城垠,致川陆之百物,富昆明之众民。”今昆明二环南路边有船房小区,昔日因水城中舟辑来往,停舟住宿,“常系船于房前屋后而得名”,这与历史上的苏杭水乡风光何其相似。今东起书林街,西接东寺街的“鱼课司街”,就是唐代南诏时在此设立征收鱼税的官家机构“鱼课司”而得名的。
直到20世纪50年代甚至80年代,城西的黄土坡、大普吉,城东的大板桥、羊方凹,城北的下马村、岗头村、龙泉镇,城南弥勒寺、西坝、南坝一带,多为农村,广布稻田。20世纪60年代中期,笔者在西山区大渔乡大渔村参加“四清”工作,曾亲见村民乘船在滇池中收割水稻,因种稻时田在滇池湖畔,成熟时滇池水涨,只露稻穗于水面,故需乘船获取。如今大渔村已远离滇池,不复有此景也。今城南北京路与春城路之间,原为吴井乡驻地南窑村,“因地处城南,村中建有石灰窑数座,故名”(《昆明市官渡区地名志》第61页),20世纪90年代初,此地尚为农村,田园广阔,阡陌纵横,而今为繁华市区。
了解昆明水城的历史地貌,以古鉴今,对于当前和今后昆明城市建设特别是宜居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建设,以及城市排涝、旅游发展等都是有益的。
本文原载《云南日报》年3月19日第7版
编辑:耿嘉蒋敏
策划:耿嘉蒋敏杨文江王晓卫
制作:王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