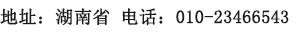龙陵被誉为“滇西雨屏”、“雨城”,这绝非浪得虚名,这里年均降雨量约为毫米。“雨城”的称谓更为出名的四川雅安有“雅安天漏”的说法,百度一看,年均降雨量约毫米,如果统计数据没错的话,龙陵就是女娲补天时施工的死角!龙陵一下雨,天庭的水表转得那叫一个快!
上苍是如此眷顾龙陵!由怒江、龙川江两江环抱,有苏帕河、勐梅河、绿根河等多条河流汹涌澎湃,还有无数条丰沛的小河溪流密布全县各个角落。
据说曾经有北方人到滇西,嘲笑我们没见过世面,随便一条小溪都敢称“江”。我都不稀罕用水流量去与之一辩了——有些“江”只能淹没磕膝头,大而无当!有些季节性河流,干涸后好意思称“江河”?我只(身体前倾45°)问一句:你们家的江河水敢喝吗?
龙陵的水若仅用于饮用,那实在太多了!龙陵的大小水电自然数不胜数,在现代文明进入龙陵之前,龙陵人民便已将中华古代智慧的水能运用普及到了各个角落。
我老家一箭之遥就有一个山谷口叫“懒碓洼”,洼即山洼,而“懒碓”就是水碓,因为原始的水能转换较慢,慢慢悠悠,故得名。八零后的我无缘得见懒碓洼的懒碓,初中毕业那年被父亲送到勐堆的亲戚家中“体验生活”,跟姨兄姨弟背着苦荞和稻谷去脱壳磨面,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懒碓和水磨。
木城乡花椒村坪子寨的水碓
水碓比较原始简单:一根中间有支点的杠杆,前面有起伏落在碓窝里的舂碓杵棒,后头有一个水槽,水槽蓄水之后重力抬起杵棒头,然后水被倾斜角倒光,杵棒头落下砸在碓窝里的粮食上以脱壳,循环往复,直到木头朽坏。
水碓一般设一排,此起彼落,流水声和舂碓声交织,“哗啦啦~~~”“咣当啷嗤!”,“哗啦啦~~~”“咣当啷嗤!”……中间夹杂着承轴的吱吱咯咯声。(水槽位置为脚踏板的称为“脚碓”,靠的是生物动能,属于舞蹈范畴,不再跑题赘述。“舂碓狗”这个词也必然牵出无数故事,荣后慢慢回忆)
龙新乡雪山村的水碾和水磨
水碾和水磨则要复杂得多,它们有一个隐藏于地面之下的巨大水轮,带动上面的石碾或石磨转动。水碾又叫“碾子”,也用来给粮食脱壳,不过效率比“懒碓”要高,属于“高科技”,只是对水流量要求很高,能建碾子房的河不但流量大,流速也要很快。“懒碓”和碾子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可以无人值守,基本上和一些自动游戏外挂是一样一样的——水磨就不行,虽然也有自动加料的斗,但容不得我们去吃一餐野果,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水磨并不是多了不起的发明。
龙新乡雪山村的水碾水磨群
我曾经在小雨中撑一把伞坐在独木桥上,把脚浸在小河中,听着碾子的水车被哗哗的水流推动叽叽咯咯的声音。迷蒙的雨中,仿佛看见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老祖宗,我的十八辈祖宗们,佝偻着身体,背着沉重的粮食,影影绰绰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在叽叽咯咯的节奏中踏着人生的节拍,渐渐远去,远去……
如今,龙陵只有木城乡的花椒村坪子寨(香堂人寨子)重建了几个水碓,龙新乡的雪山村——大雪山下一个风光如画的村子里保留下一个水碾水磨群,前几年我去的时候已逐渐破败,不知现在可好……
如今我们“现代化”了,水碾水磨已经太过原始(说到此处,“懒碓”一脸尴尬)。落后就要被淘汰,这是历史的法则。然而,在生产力之外,人类称为“生活”的东西并不仅限于效率,它有自己的旋律,需要一个合拍的节奏应和。
我记忆中的那个节奏就是:“哗啦啦~~~”“咣当啷嗤!”,“哗啦啦~~~”“咣当啷嗤!”……
来源:瞬间龙陵苯丁酸氮芥说明书北京中科医院诈骗曝光